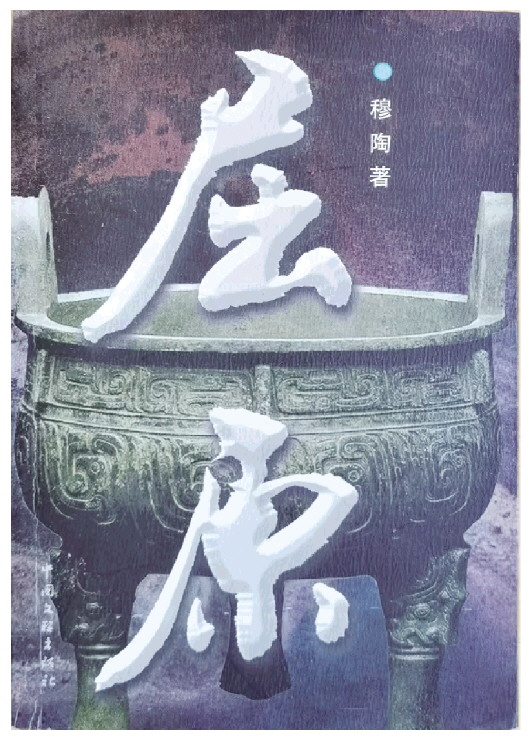
穆陶著作《屈原》
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屈原》,穆陶经过数年研究考据,厘清屈原与周遭人物关系、楚国风俗人情以及所处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为屈原塑造了政治家和诗人的多维度形象。作品于2002年出版,文学界好评如潮。《屈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在海外华人圈引发持续热议。
数年阅读大量史籍 厘清屈原人际关系
2002年,穆陶的第五部长篇历史小说《屈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在华夏大地,屈原的名字早已与端午节紧密相连。每逢农历五月初五,龙舟竞渡的鼓声、粽叶飘香的气息,都在诉说着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屈原忠心辅佐楚怀王,却遭奸臣构陷,被流放他乡。满腔悲愤之下,他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楚国百姓纷纷驾舟搜救,又将米团投入江中以防鱼虾侵害其尸身,这便成了今日端午龙舟与粽子习俗的由来。
传说是事实的牵强附会,而真相则往往扑朔迷离。以屈原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其生平事迹,除了汉代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新序》留下了大致相同的简略记述,几乎再无什么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他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风貌、礼仪制度、物质文明与地方风俗,在文献典籍中或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后世研究更是莫衷一是。
穆陶为还原屈原与他的时代,一头扎进史籍的海洋,光是精读与浏览的核心参考文献便达30余种、数十册之多,从《战国策》《楚辞》到近代学者的考据论著,字里行间都留下了他批注的痕迹。
经过数年爬梳剔抉与分条析理,穆陶终于厘清了屈原与周遭人物的复杂关系、楚国独特的风俗人情,甚至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成功缩短了古今之间的认知隔阂。比如,他考证出屈原与宋玉并非简单的师徒关系,更蕴含着文学传承的精神共鸣;楚怀王与郑袖的宫廷纠葛背后,暗藏着楚国贵族势力的权力博弈;就连“上官大夫靳尚是一人还是两人”“庄蹻(qiāo)是楚国将领还是起义领袖”这类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谜题,他也结合史料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读。在此基础上,穆陶以“于史有征”为准则,用文学的笔触为屈原与他的时代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以史为核融入情感 致敬古人照见当下
“历史小说要体现‘史’的内核,就必须忠实于基本历史框架。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史’的骨骼与作者的思想情感血肉相融。当《屈原》中的人物带着他们的爱与恨走进我的情感世界时,我忽然觉得,他们身上的古意不再遥远,他们的喜怒哀乐或淡如水,或浓如血,或缠绵悱恻,或壮怀激烈,都让我忘记了时空的阻隔,仿佛他们就活在当下。”穆陶在《我写屈原(代跋)》中的这段文字,道出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精髓。
正因屈原的史料稀少,反而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穆陶塑造了一个多维度的形象: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活动家,力推宪令以图强国;又是“发愤以抒情”的伟大诗人,《离骚》《九歌》在书中化为与命运对话的心声;更是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坚守着对“善”与“和”的信仰。在屈原逐渐成为抽象文化符号的今天,穆陶着重刻画其具体的生命轨迹:他如何在朝堂与奸臣据理力争,如何在流放途中体察民间疾苦,如何在绝望中保持精神的挺立。书中郑袖为争夺王后之位,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恳请屈原为她撰写祷词。屈原朗声大笑:“郑袖你听着,我的笔墨只为天地灵秀、人间真情而作,决不为罪恶辩护、为丑恶唱颂;我的文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岂容肮脏灵魂玷污其芳洁!”这番话虽带些许现代语感,却精准击中了屈原的精神内核,也暗藏着作者对坚守者的敬意。
细节中更见匠心。屈原与侍女婵娟谈及战国变法时,评价吴起:“其变法过于峻急,重‘战’轻‘和’。我要拟定的宪令,既要利耕战,更要养善性,终让人心归‘善’,方能消弭战争,成就太平世界。”这段独白与其说是屈原的政治理想,不如说是穆陶对人类文明的思考。正如他所言:“写《屈原》的过程,像一场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我追随着那个遥远的身影,也在字里行间照见了当下的自己。”
推向海外好评如潮 架起古今对话桥梁
《屈原》一书油墨尚未干透,这部作品便如一颗投入文坛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韩国出版界闻讯,迅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取得联系,推出韩文版《屈原》,让这位中国诗人的故事在汉江之畔落地生根。
《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小说进行了连载,使屈原这一形象跨越重洋,遍及五湖四海,在海外华人圈引发持续热议。学术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穆陶的《屈原》,是自《桃花扇》《李自成》以来,又一部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一脉相承,又在历史深度与人性刻画上有所突破与创造。”
《屈原》问世后,文学界好评如潮。著名学者曾敏之在书评中写道:“穆陶以诗性笔触重构了屈原的一生,让这位伟人从传说中走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部作品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不仅写活了历史,更接通了古今精神的血脉。”他特别称赞:“穆陶将现代叙事技巧与古典意境融合,文笔简劲如剑,刻画精微如绣,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文艺报》罕见地连发两篇评论,足见学界重视。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朱辉军指出:“屈原身上凝聚的刚毅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穆陶的写作没有停留在复述历史,而是让这种精神在当代苏醒——我们怀念屈原,正是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而《屈原》一书,让这种力量穿透了时光的帷幕。”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则从文学性角度分析:“小说对屈原的武功文治、宫廷争斗着墨不多,重心全在展示他在困厄中的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本心?是屈膝求生还是以身殉道?这种对人格操守的深度挖掘,让作品超越了普通历史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人性与信仰的寓言。”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刘伟生的比较研究颇具见地。他将穆陶的《屈原》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对照,认为:“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烈火焚身的诗人’,激情澎湃如火山喷发;穆陶则让屈原站在政治与思想的双重维度上——他既是‘上下而求索’的诗人,也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政治家,更是思考文明走向的思想家。这种定位更贴近民众对屈原的集体想象,也让人物更具现实观照意义。”刘伟生在文中强调:“《屈原》的成功,在于它没有停留在‘讲好故事’的层面,而是始终追问: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什么?生命的价值何在?现代人该如何安放精神家园?这些追问,让一部历史小说有了照见当下的力量。”
从国内学界的专题研讨到海外华人的读书会,穆陶的《屈原》如一座桥梁,让两千年前的屈原与当代读者相遇。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伟人的生平,更是一个民族对精神高地的永恒守望。这种守望,正是历史文学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文/图 孙贵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