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应忠演示抄纸

竹山边的料饼晒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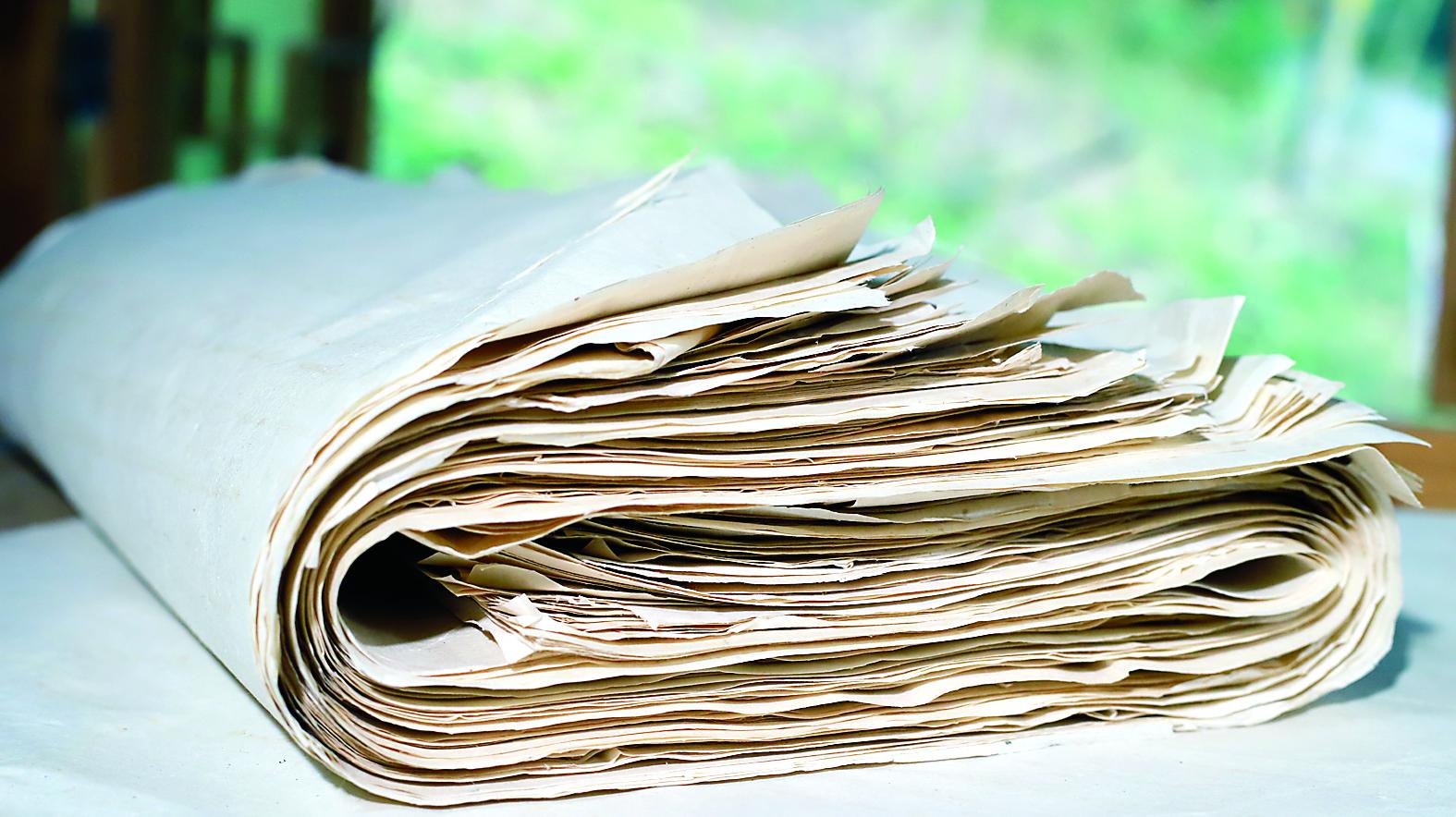
试制的连史纸

阳光正漂白竹纤维料饼

捶过的料泥

连史纸
在邵武连史纸制作技艺恢复后,听闻近日第二批邵武连史纸即将面世,我们专程驱车前往邵武市大埠岗镇乌石村一探究竟。途中,竹林与山峦交错,百步之外仍是满眼苍翠。这像是一次叩问竹海、得见纸乡的旅程。
乌石村数百年来静卧于万亩竹林之中。18世纪末,其僻静的地理位置与气质,受来华洋人青睐。美国人在村里西崖顶山腰处建立了避暑山庄与教堂。
如今,乌石村因为一张纸的名字,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村里的三位传承人以本地毛竹为原料,成功将历史上享有“纸寿千年”美誉的连史纸“带回”现代,接续了邵武与连史纸制作技艺的百年之缘。
竹海无垠藏纸乡
近两小时的车程之后,从邵武市区出发的车辆终于驶进乌石村地界。山连着山,车窗外已是竹的海洋。随着绿色波涛穿进这片无垠竹海,乌石纸坊展现在眼前。
连史纸的历史,在文献中早就有迹可循。1934年,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的《福建调查统计专刊》曾记载,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福建各地销售二十多种纸,其中邵武、泰宁等地都有“连史”纸销售。
在明代,邵武已吸引外地纸匠前来学习造纸技艺。龙岩市连城县姑田镇是有名的宣纸产地。天启六年(1626),姑田镇人蒋少林在邵武县向当地人学习造纸技术,掌握蒸煮竹丝、天然漂白、打浆方法和造纸、烘干等工艺过程之后,于崇祯二年(1629),回到姑田,利用当地出产的大量毛竹,试制成功天然漂白的手本纸。其时,邵武纸业发达可见一斑。
乌石村人将其制造的连史纸视为荣誉。乌石村熊氏族谱记载,民国四年,村民熊灵昌曾带着连史纸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受到农商部嘉奖。“一船纸销去南洋,能换回一船大洋。”乌石村党支部书记、邵武连史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熊应忠复述着祖辈口耳相传的故事。可见,连史纸曾从山村走出国门,带回来财富,也见证过辉煌。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乌石村里,仍保留上百个纸槽,上千人从事造纸及相关工作。至今村里仍有清朝时期遗存下来的3口煮竹丝的旧锅及蒸煮房的遗址,默默见证着此地纸业往昔的辉煌。
技艺接续克百难
造纸坊前,垂挂着一排排竹丝,山泉潺潺流入浸泡池。“浸泡池和纸槽里的用水都来自山上。”熊应忠介绍,制作连史纸的材料来自立夏前后的嫩竹,砍成大小合适的竹段,从下至上、由厚到薄堆放,并且在山泉水里浸泡数月。微生物逐渐分解着竹子中的糖分,直到竹皮可轻易剥落,竹肉也可以轻易分离成竹丝。剥下的竹丝在晾晒后,像一把把白色的线面。再经过“三蒸三晒”后,按照古法,竹丝会被制成直径约六十厘米的竹纤维料饼,摊放在山间的晾晒架上。阳光作为“漂白剂”,雨水则能洗去发酵残留的物质。数月后,竹丝洁白如雪。
邵武连史纸制作技艺久不应用。时隔半个世纪重新“拾起”这门技艺并付诸生产,千头万绪。
熊应忠既是村支书又是乌石村人,对他而言,解开这团乱麻的动力来自一代代流传的情感。“我们乌石村世代造纸,就连家里的族谱也是用连史纸做的。”熊应忠说,尽管技艺已经断代了数十年,但是父辈的家里仍然保留着制作工具。乌石村和造纸业割舍不开。
2022年11月,邵武市启动恢复古法制作连史纸项目。乌石村成立了一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购置抄纸竹帘、打浆木槌、纸槽等,建造乌石古法造纸坊;同时,邀请村里三位老纸匠熊木进、张荣祥与熊诒荣“出山”相助。熊应忠、熊建平、梁志楠一同向老纸匠学习邵武连史纸制作技艺。
几十年前,老纸匠在生产队生产连史纸。张荣祥还曾担任村里造纸生产队队长。如今三位老人都已年过八旬。张荣祥与熊诒荣已体弱力衰,对教学工作力不从心。身子较为硬朗的熊木进承担了大部分教授技艺的任务。“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如果现在不好好学,以后不知道向谁学了。”熊应忠说。
“纸张的薄厚、平整、均匀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法。”熊应忠介绍,他们现在的手法还不算纯熟,需要多看多学。在纸槽前,熊应忠拿起纸帘,演示抄纸。纸帘从池面斜抄起,涟漪的边缘扫过纸帘。“水完全从纸帘渗下去。抄纸三次,就有三层纤维交叉。”熊应忠解释道,这就是连史纸轻薄而坚韧的关键。但仅靠口传心授,徒弟们难以完全领悟。他们也要翻查志书、文献,还到宣城、连城、铅山等各个手工造纸产地观摩学习、多方讨教。
2023年6月,纸坊通过连史纸制作技艺试制出纸。同年11月,邵武连史纸制作技艺被列入南平市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4年为了试验本地竹子造纸的可能性,我们跳过了自然漂白的步骤。虽然那批纸张没有达到理想的均匀度和白净度,但我们今年已经准备好新的造纸原料。”熊应忠期待着,今年制作出品质更好的连史纸。
非遗传扬道阻长
一张纸,其上的墨迹能存留多久?
连史纸给出的答案是“千百年”。
在南平一位收藏家手中,保留着几份在乌石村发现的卖地契约、借款字据等文书,落款时间有万历九年三月、嘉庆十九年二月、道光十二年十二月……。这些文书边缘略有破损、毛边,但大体完整,墨迹清晰可辨。这些留存至今的文书,让连史纸“连绵史册”之意有了具象的体现。
有人认为,“连史纸”最初可能是“连四纸”的讹传。但无论名字的由来如何,它“纸寿千年”的品质,确实为历代文人称道。
连史纸轻薄坚韧,色泽洁白,久放不黄。用它书写绘画,字迹清晰,读来眼睛不累。用于拓碑钤印时,纸张服帖,能完整呈现石刻的细节。
然而,进入20世纪,机器造纸兴起。工业化的纸张价格低廉、产量巨大,平整度和白净度也超过手工用纸,很快占据了多数市场份额。手工纸坊日渐式微,邵武手工纸业逐渐衰落。20世纪70年代后纸槽遍村的现象不复存在,技艺传承几乎中断。
纸坊里,几位传承人轮流为我们讲解、演示抄纸、焙纸的工序。与江西铅山已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分工生产的“连四纸”相比,乌石村还处在“一人多岗”的起步阶段。“我们现在是哪里缺人就顶上,备料、抄纸、焙纸等所有环节都要试。”熊应忠说,等以后有人愿意学,才可能细化分工。
连史纸的“复刻”之路,也离不开验证和对比。熊应忠拿起一张带有“乌石纸坊”水印的连史纸,轻轻摩挲纤维的纹理。“与遗存的老连史纸比较,新造的色泽、平整度尚有差距。”熊应忠说,不过,南平市书法家协会与邵武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都对新纸有良好评价。
关于技艺的未来,三位传承人心里也有忧虑,比如年轻人接手的意愿微弱。“这次我们会全程录像,详细记录工序,至少能让年轻人知道祖辈的手艺。”梁志楠说。熊建平动情地补充:“这是父母供我们吃穿的本事,不只是赚钱的买卖。我们得想办法捡起来、传下去。”
“最终的目标是稳定生产,实现盈利。我们乌石村来钱的路不多,竹子是村里最大的资源。造纸是很符合现状的产业。”熊应忠顿了顿,“不过眼下,我们更急的是把这门手艺留住。只要技艺在,机会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