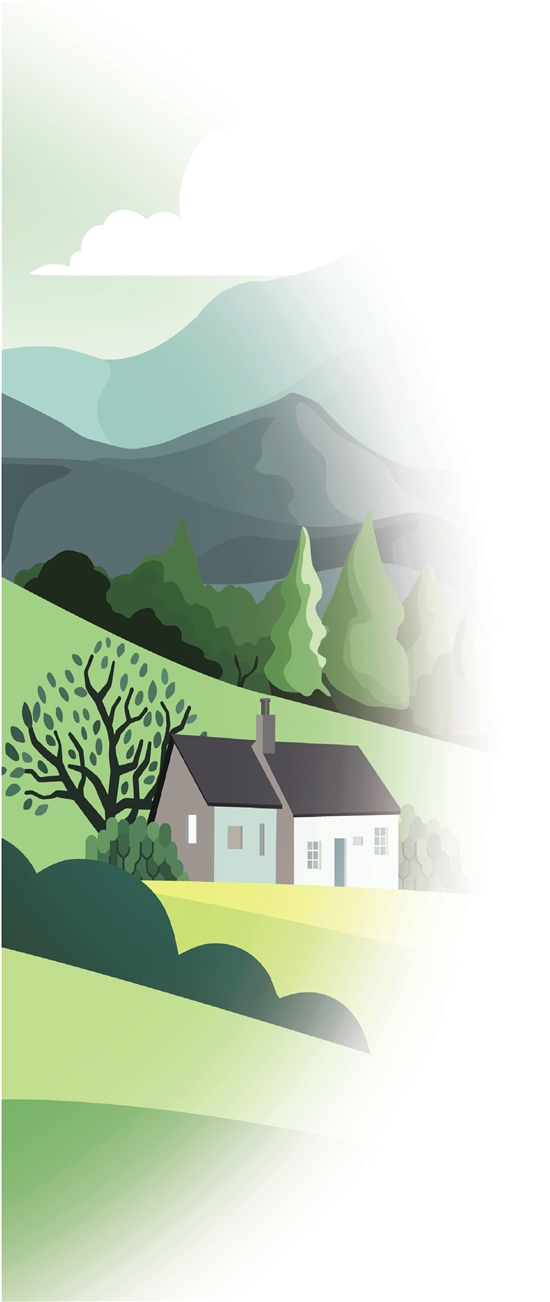
陈大才
这次回老家是在母亲多次“哀求”下才作出的决定。临行前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絮絮叨叨地交待了很多,我恍惚间只是记住了“给长辈晚辈包个红包,多请一天假”等些许内容。
听着导航,车子在弯曲的山路飞奔,看厌了城市林立的高楼遮掩下的那小抹绿色,群山的碧翠令我有些陶醉。摇下车窗,耳畔满是呼呼的风声,夹杂着惊飞鸟儿的聒噪。
我陷入了回忆,儿时的家乡是山腰间的一个村落,一条黄泥路蜿蜒地通往远方的乡镇。记得儿时,每每遇上赶集,母亲总会挎着装满鸡蛋的篮子到市集去卖,而我和几个小伙伴总是一溜烟地来回跑着,扬起的黄尘引来母亲们的轻声喝斥,我们则在叉路口讨论着这条路会通向哪里。日暮时分,小伙伴们疲惫地跟着母亲,慢慢地走着,到了村口,正值牛羊晚归,稍大的伙伴向放牧的伙伴炫耀集市上的奇闻趣事,而稍小的我则追逐起牛羊,引得它们四处乱窜,俨然一幅“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景色。
堂哥佝偻在村口的路旁,我踩下刹车,有些许愕然地喊了声“哥”,邀请他上车。在堂哥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一幢楼房前,将车停进院子里,进门后看见一个小女孩坐在垫子上独自玩耍。看见陌生人,小女孩羞涩地躲进房间。
堂哥告诉我,这是老三的女儿,现膝下共八个孙儿外孙,言讫便进屋领孙女去。我翻开皮夹,才想起红包准备得不够,有些后悔没听母亲唠叨,便在微信中给堂哥按人数发了个红包,从车上取了一包饼干递给小女孩。小女孩低声地喊了声“爷爷”,接过饼干,咬了半块便放在桌子上。无糖饼干,小孩子都不会喜欢的。我暗自忖度,我那时吃的零食都是纯天然、零添加的。每每放学回家,母亲都会高声叫道,快去放羊,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而圈里的羊听到声响就会卖乖地“咩咩”叫唤起来。我便扔下书包,拉着母羊,领着小羊,喊上伙伴,一起出去,找到各自分好的“领地”插下羊销,便一起干“坏事”。春天刚种的番薯,夏天的嫩豆角、黄瓜,秋天树上坚实的板粟、涩嘴的柿子,反正不“偷”自己家的。
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小孩子偷嘴,大人们只能吆喝,不能追更不能打。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便吃得肚皮滚圆,还相互攀比谁的肚皮大,吃不完也不打紧,全用石头锤烂给羊吃。日薄西山,便赶着羊群回村,羊群多了,老羊识圈领着羊儿径直回家,我便抱起最小的羊羔防止走丢,羊羔舔食着我手中残留的番薯汁,母亲们则呼唤自己娃儿的名字回家吃饭,这场景用“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形容最为贴切了。
午饭后,便想开车去看望舅舅,可车钥匙找不到了。堂哥打趣道,孙女看车钥匙漂亮拿去玩了,现在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将就住一晚,明天再走吧。看到堂哥“狡黠”的笑容,我才想起母亲叫我多请一天假的缘由,质朴的人们总是用最“蹩脚”的借口挽留他们心目中最“尊贵”的客人,我没有点破,便沿着房边的小水渠寻找山顶的那条小河。
儿时的村庄傍山而建,山顶有条小河日夜欢腾,勤劳的人们便凿了一条宽宽浅浅的小溪,引河水入溪,溪水潺潺流入各自家门的小水渠,在院内掏一洼小池,细心的人们在小池出口扎上密密的篱笆,洗菜的剩叶捞起来喂养鸡鸭鹅,池水还可以浇灌院里的白菜、莴苣、油菜。暮春时节,正值农忙,各家的院落内洒满了黄的白的小花,我和小伙伴便可以从这家院子窜到那家院子,尽情地追赶捕捉飞舞的蝴蝶。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脱口而出“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离开家乡,来时的路便是回去的路,眼前的景致不情愿地向后飞驰,正如时间般流逝着。家乡,经过岁月的洗涮,已不是儿时的旧模样。我,不应再称呼她为家乡了,应当称为故乡,故就是过去,过了就回不去了,但她照样也会写进别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