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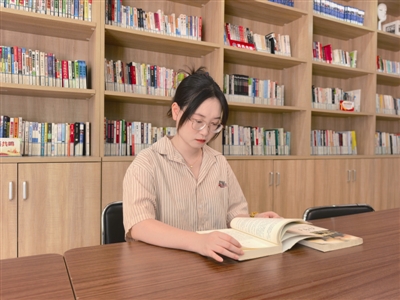
冷菲钰:
滨江新区办事处康阳社区网格员
影响较深的一本书:
《活着》
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将玫瑰藏于身后,风起花落,从此鲜花赠自己,纵马踏花向自由。
看余华的采访,像是在开盲盒,总有惊喜,让人忍不住感叹他的幽默。这与他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截然不同。在书里,他总是将社会血淋淋地剖开,将现实摆在读者面前,因此看余华的作品,时常感同身受,内心酸涩。
余华曾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真实的世界是残酷的,但现实的残酷照见人为求存所做的各种努力。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各种生死离别,最终被孤零零地留下了。回顾他的人生路程,字字泣泪:战争爆发后,他被抓了壮丁,上了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捡回一条命,好不容易回到家,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因发高烧变成了哑巴。此后,儿子有庆因献血过度而死,女儿凤霞怀孕难产大出血而亡,甚至女婿、外孙也离开了他。看到他一个人赶着老黄牛苦苦度日,很难不令读者共情。是悲书中事,也是怜书外人。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宣言,余华用最朴素的文字叙述出最深刻的道理——活着或许没有意义,但“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生命对世界最执拗的回答。当所有外在的支撑都崩塌后,生命依然会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
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靠卖血来完成了许多人生中的大事,为了结婚卖血,为了让挨饿的儿子和老婆吃顿好的去卖血,因为一乐打破别人的头要赔钱而卖血,为了弥补被自己占了便宜的林芬芳卖血,为了请二乐的生产队长吃饭卖血,为了给两个下乡的儿子补补身子卖血,为了给一乐治病一路从家里卖血卖到上海,总算救活了儿子。许三观面临困境时的挣扎和抉择,是生活中每个人的缩影。
如果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借小说人物及故事来折射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七天》几乎零距离地逼近社会现实,作者将社会热点事件纳入作品的叙述视野。作品试图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场所里来展现当下的现实景观,出租屋、废墟、医院、油污的小餐馆、派出所、发廊、商场、村庄等被包罗其中,贴上现实社会的脸颊。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余华像收藏家一样搜集案例和事件”,作家是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态来书写现实。
余华的作品总能给我一些现实性的思考。如其所言:“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冷菲钰口述 孙圣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