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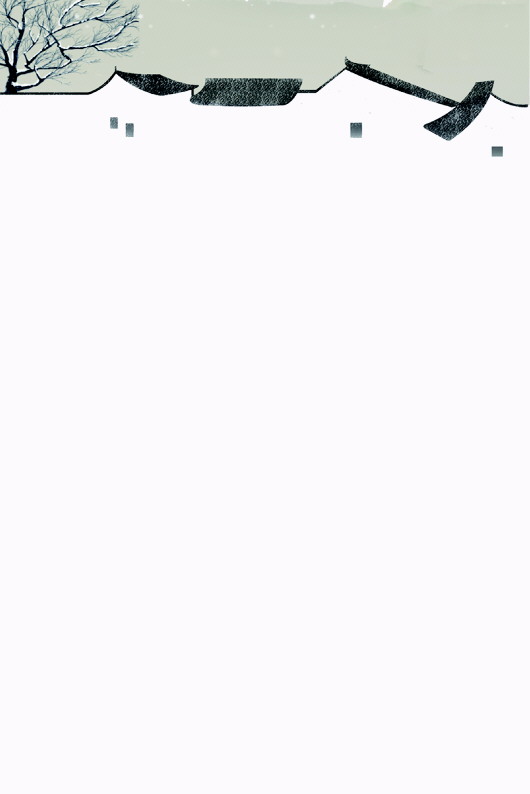
□ 王勇建
儿时的记忆里,每当冬意渐浓时,小城家家户户的房檐下,便会伸出一截冒烟的铁皮烟筒,像极了嘴角叼着一支粗重的烟卷。闹市区有处叫“爷坑”的地方,杂货铺门前总堆着黝黑的铸铁火炉,旁侧立着几摞锃亮的铁皮烟筒,在冷光里泛着暖烘烘的期待。来挑火炉的人裹着厚棉袄,一边跺着脚驱寒,一边搓着手寒暄,话里话外都是“今年冬天怕是要比往年冷些”的絮叨。
“爷坑”上空总飘着“踢里哐啷”的声响,那是市民挑拣火炉烟筒时,金属碰撞出的“锣鼓”声,热闹得很。很多时候,烟筒的销量总比火炉好——谁家的铁皮烟筒不是宝贝?保养得仔细些,熬过一季寒冬,来年擦擦还能再用。那些半米来高的铸铁火炉,炉身上顶着圆的或方的炉盘,盘上套着两个圆环、一块圆饼,做饭时按锅的大小添减,方便灵活。不管是新炉还是旧炉,用前总得泥炉膛,红土掺上少许头发和成泥,长辈说,这样的泥耐高温,还结实。炉膛泥好,男人便搬张椅子站上去,一节节接烟筒,女人和孩子在底下扶椅子、递东西。“7”字形烟筒刚安好,孩子的脸上、手上已蹭了好些煤灰,你笑我,我笑你,笑声裹着煤烟味,飘得满院都是。
当第一缕青烟从房檐下的烟筒里钻出,小屋就暖和多了,再也不用缩手缩脚。20世纪80年代的大杂院,一到冬日,各家炉火齐燃,淡蓝的烟雾笼罩着整个院子,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烟火图腾。原本冷清的屋子,支起火炉便活了——床板挪到炉边,屋外小厨房的案板、锅碗瓢盆也挤过来,巴掌大的地方顿时被家什塞得满满当当,日子的烟火气也顺着炉缝钻出来。一进门就知道,中午炉上炝过浆水,傍晚蒸过萝卜馅包子。
母亲总在炉边忙活冬日的烩菜。切白菜、削洋芋皮、泡粉条,水汽氤氲着,把窗户蒙成一片白雾。炉上的铁壶咕嘟咕嘟烧着水,灌满地上的两只保温瓶,再续上凉水,不多时又冒起热气。屋子里润润的,洗菜刷锅再也不冻手,连空气里都飘着暖融融的水汽。我总缠着母亲,切几片洋芋薄片,贴在滚烫的炉身上,不到一分钟,薄片就焦成金黄,塞进嘴里“咯嘣”响,那股子清香,是冬天独有的滋味。个头大的洋芋切块炖进烩菜,小个的就被我们扔进炉底的煤灰膛,半小时后,烤洋芋的香味儿就漫了满屋。洋芋外皮烤得焦黑,掰开却是沙绵的瓤,香得人连姥姥的叮嘱都忘了。
尤其飘雪的日子,裹着厚衣裳踩雪回家,“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落在雪里,推开门看见炉膛里的火还旺着,就再也不愿挪步。把手搭在炉上烤一会儿,把脚凑过去暖一暖,或是窝在弹簧沙发里打个盹,再冷的天、再累的事,都成了过眼云烟。那时手机尚未普及,却从不觉得孤单——母亲在搪瓷盆里和面,面团揉得“砰砰”响;父亲倚着沙发,就着炉光看书;哥哥伏在台灯下写作业,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我呢?大概是在炉边追着火星子跑,或是蹲在地上扒拉烤洋芋,只要一家人围着炉火,再调皮的我,也会变得安安静静,觉得那一刻,是一天里最踏实的幸福。
还记得某个半夜,我被嘈杂声惊醒。屋外大风呼啸,煤烟顺着烟筒倒灌进来,父亲和母亲披着棉袄起身,开窗、捅炉子,动作很轻,生怕吵醒我们。朦胧中,我看见他们在风里忙碌的身影,母亲过来掖被子时,手是冰的,可我心里,却暖得发烫。
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心里的炉火仿若再次被点燃,任凭时光流转,心底温热的火苗从未暗过,把那些冬日的暖,焐成了一辈子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