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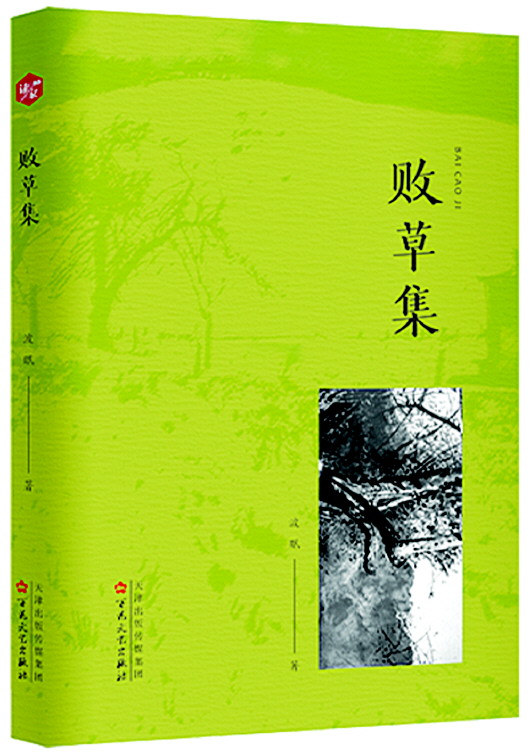
□ 波眠
这是近些年我陆续创作或发表的诗,出于文人的积习,把它们收拢在这本《败草集》里。我不大会电脑操作,收集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往昔的诗已经找不见了,已然如草叶一般散于尘埃当中,像我掉落的头发,它曾经在头顶上泛着自己血脉的光芒。
我本是农民出身,在农村生活二十余年,成家生子后才进城工作,又开始所谓的城里人生活至今,我所受的学校教育也有限,所有的价值伦理认识和情感积累都来自我的少年乡村岁月。
我写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那些大地上的亲人们,他们的坚韧、勤劳、柔顺,他们的善良、苦乐、不幸、无助,在商品经济时代的无所适从似乎永远都是我关注和感念难忘的对象。我与他们本来血肉相连,他们骨子里的土地道德,对水土的敬畏是我挥之不去的精神乡愁。我有时只是粗劣地描摹与记述,感伤喟叹,未能过多考量诗艺的别开生面或标新立异,也没有仅仅为了见刊发表而削足适履。现在看来有些写得粗劣而平庸,也许山地间长大的我骨子里缺少纵横,缺少酣畅与所谓现代观照,即便是这样,那些夜灯下的短句依然有一丝隐隐的忧患和淡淡的哀愁。
泥土本来简单而朴素,深厚而神秘,它的因子元素自然形成了我诗歌地域水土自然山色的肌体内蕴,如果我写了泥土的天籁丰饶,那也只是拙劣地从自然当中采撷和嫁接而成,这种写作我曾自嘲为狭隘的写作。一个乡下人写他的乡村图景,既顺乎自然又乐此不疲。乡土对我而言不是一个他乡人浮泛的流行概念,而是我身边绝大多数人生命的维系与存在,何去何从?经常是诗歌的尽头茫然未知。对那些掏空了矿石的疲惫的山体,对越来越变得浑浊的水流,对落寞而陌生的故乡,我的焦虑一直在递增;纵然有更多的人间业绩需要赞颂,但我讨厌未经生命嵌入的作秀和制作的故弄玄虚。我永远记着诗人何来老师给我诗评写的一句话:“诗不关注现实,现实生活就必然不关注诗,逻辑是不是就这样简单呢?”
在诗歌的社会性和现实感日益消解的当下,对我而言带墒的泥土仅能生长一些杂花野草,但它们有着泥土的脉息就够了。感谢诗歌给我生命的快乐和生活的慰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