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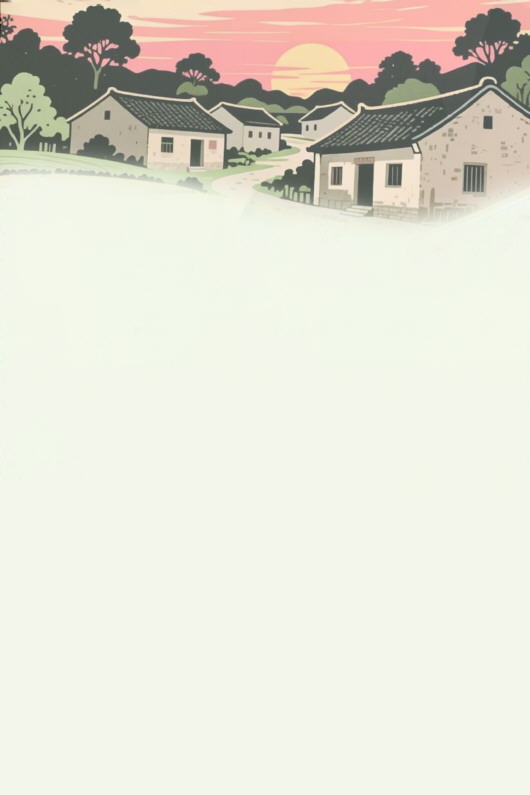
□ 孙德虎
今年正月初一,天水孙家坡村,瑞雪飘飘,吉兆丰年。
比平日晚起的男女老少,等燃响喜庆的鞭炮声后,各司其职:老少清扫房前屋后的积雪,婆媳料理新年第一顿丰盛,青壮年不约而同奔向村庄主干道,一帚一锨,一片一段,接起扫雪长龙。
雪花里热闹开的新人新事,由务了60亩花牛苹果走俏春节的回乡创业青年,到开回来一辆苏A牌新车的打工厨师,到从事无人驾驶、扫雪动作略显笨拙的“北漂创客”,再到“村晚”彩排的一长串节目,一时间,铺陈在雪景中的家事村事,好像“朝闻天下”——现代农业的,消费升级的,人工智能的,精神欢娱的,都紧贴着国家大事脉动。很快,你一言,我一语,又滑向一副春联——“百年黑娃名孙健,寻亲红军是我家!”
“喜录哥,你突然贴出来一位老红军,差点惊掉我手里的扫帚!”
“我越看越好奇,只想问清楚,你怎么知道老红军的?为先烈寻亲,可是大事,不是闹着玩的。”
“啥?1936年的红军,那,那肯定参加过北上抗日?东渡黄河了没有,参没参加过百团大战?”
“辈分不对吧?老红军如果健在, 那都110多岁了,你才叫堂四伯父,弄得我们称呼起来,很不过瘾。对打江山的英雄,你就不能再高一两辈吗?”
“春联的内容,不像是你想出来的,要不,你就当众讲,能讲清老红军的抗战史,我们这帮人,就尽义务,去光荣军属家扫雪。”
……
刚张口解释了一星半点,又被一个个问题接连噎喉的孙喜录,像口里含着一块宝贝疙瘩,吐也不是,咽也不行,喉结一上一下的,眉头一舒一皱的,看看这个的情绪激动,又望望那个的喜不自禁。
终于有机会了,他才略带伤感又不无兴奋地说:“我的堂四伯父,走出去后就再没回来!当红军的事,要不是村里走出去的文化人偶然看到党史资料的简载,回老家大海捞针,反复盘询多个老人的口述,细细比对年龄,才分辨出名字,还纪实书写了《你若记得,他便无悔——老家百年红色记忆采访手记》,我这个小名叫黑娃,30多岁流落在武山县鸳鸯镇,会点武术,又做过木匠的伯父——1936年8月前后参加红军的孙健,恐怕,就永远‘走丢’了!”
“三大红军主力长征,都经过天水,胜利会师后北上抗日,到现在,有整整四代人了,我们还能通过一丁点儿信息,追寻到当年的老红军,幸亏,幸亏有党史工作者,和村里老人的口述。”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把老人家的说法,只当闲言碎语来听,说不定,里边还隐藏着村里走出去的更多的抗战英雄呢!”
“是啊。前几年,老支书的葬礼上,一副‘稳庄打成四座坝,致富不忘一片心’的挽联,就激活了一位抗战老兵——老支书的父亲孙进财。”
“我记得,当时说起的,还有参加过抗战的孙世忠、孙贵生等4人,很可惜,他们也没有回来,我们也就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了。”
“我也记得,当时说孙进财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具体是哪些战役,口述都说不清楚。但他九死一生回来了,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儿子孙岁学也是共产党员。20世纪80年代任村支书后,孙岁学还带领大家给村里通了电,修建了4座拦水坝,整修梯田道路,造林绿化荒山,引自来水进户,今天村里的安宁幸福,真要感谢他们两代人的心呢。”
“当时老年人口述的情景,我一直记得,还掰着手指头算过,新中国成立后,从村里第一个志愿兵算起,应征入伍的,共有31个人呢。”
……
位低未敢忘报国,谁说不是呢?
一个名不见经传,也无文字史的西部偏僻村庄,总喜欢把时空折叠在口头,也喜欢把人物品评,镶嵌在红白事或集体劳动之间。可他们,有自己的“万花筒”和“纪念馆”——对村里曾经的平凡人干出的不凡事,一直口口相传,相传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传成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口头丰碑和精神长相。
而今,这些口头流播,终于流出了一副独特的春联。
丹心如春的横批,贴在村庄主干道边的门楣之上,像一束红梅,被雪景一衬,分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