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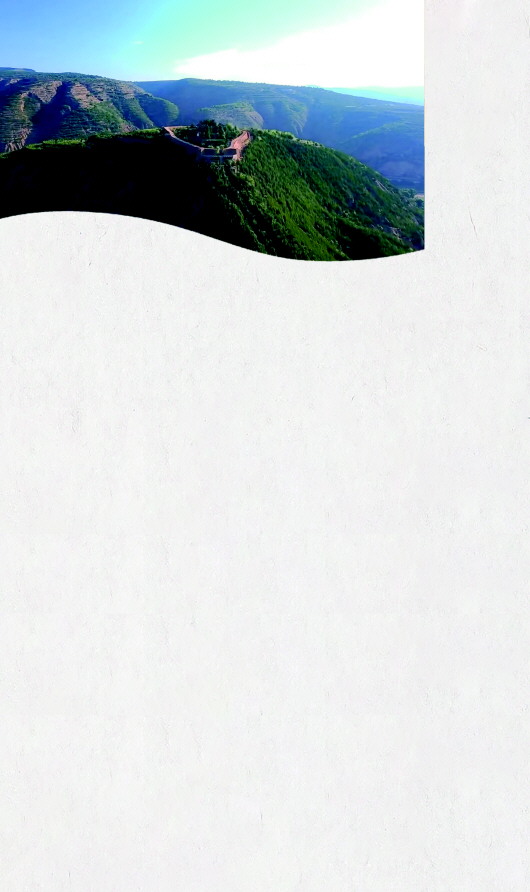
□ 徐云峰 自打记事起,常听奶奶说“挂头山”,那是在奶奶看来无比遥远、无比雄伟、无比神圣的一座山。起初,我对“挂头山”这个有点恐怖的名字心存疑惑,直到后来识字后,才知道奶奶所说的“挂头山”是她的口误,实乃卦台山。 奶奶生于民国七年,九十六岁寿终正寝。她在卦台山下生活了一辈子,出过最远的门是去三十公里外的北道埠(现麦积区),登过最高的山就是卦台山。一辈子在有限的空间生活着,奶奶却有着对人生最远的见识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奶奶生活的劲头很足,一辈子养育了八个孩子,八十多岁耳聪目明,“三高”不高,还能擀得一手好面,奶奶的擀面技术是邻居们向往的手艺,我打小吃着奶奶的手擀面长大,至今对手擀面情有独钟;奶奶对卦台山上的人祖爷十分虔诚。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从我家去往卦台山的路显得十分遥远,而“三寸金莲”的奶奶,去趟卦台山无异于一场艰难的朝圣,但奶奶依然坚持在每年正月十五步行去卦台山,一走就是大半辈子,据说这一天是卦台山人祖爷的诞辰之日。她往往在天蒙蒙亮时出发,摸着黑回来。在她看来,人祖爷是最高级别的神,往返步行十余个小时,当面磕头,一定能给家人带来福气。奶奶对卦台山人祖爷的虔诚之心,曾一次次唤醒我对它的向往,我想一探究竟,直至学会了自行车,并从父亲那里获得了骑行权,才有了第一次去卦台山的机会。 从家里骑自行车出发,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卦台山。我去的那天,依然是正月十五。卦台山脚下的农户家家都敞开大门,提供存自行车服务,只从那一家连一家院子里停放的密密匝匝的自行车来看,朝山的人不会少。那时,通往卦台山山顶的路,沿山体开凿,宽不到一米,上上下下的人分列两边,在陡峭处如登天梯,后面的人头直接挨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黄土在脚下腾起,过年的新衣服落满了灰尘,但每个人都面带笑容,大家心里至少有一个美好的心愿要与人祖爷说。 半个小时的攀登,就能到达山顶。山顶是个平坦的小城堡,四周城墙合围,中间是供奉人祖爷的大殿,殿外柏树参天,中间香炉中香火旺盛,大家纷纷面朝大殿中端坐的人祖爷磕头许愿、祈福,我也加入其中。抬头仰望,只见人祖爷目光如炬,注视前方,手持圆形八卦盘,上面的图案神秘莫测;大殿对面,搭着简易的戏台,为人祖爷唱着秦腔。我挤过看戏的人群,来到了东侧城墙,但见一条河泛着银光,曲曲折折,向东奔去,而在目光的尽头,是我村子的炊烟,那里距离我站的位置有大约二十公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高处看到家乡的全貌,看到我的村子在大地上的样子,我就像一只鸟儿,俯瞰着三阳川大地。正因那一眼,我心目中的家乡的 样子——美丽的河流,平坦的田野,轻如薄纱的炊烟构成的画卷永远定格在我的心海。 奶奶九十岁后,就再没有去过卦台山。我成了家庭代表,逢正月十五会骑自行车去卦台山朝山。去的次数多了,逐渐发现,卦台山虽然是一座绝对高度不到一百七十米的山,但只要你站在其上,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明明在山脚下看,周围的山都比卦台山高,但只要站在卦台山上,卦台山立刻成了万山之山。每每站在东侧的围墙上,便让想象的思维逆流而上,停泊在八千年前的岁月。卦台山城堡中,男人们扛着猎物回家,女人们吹着埙音唱歌,孩子们围着篝火跳舞,人祖爷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站在此处,看滔滔渭河向东奔去,想象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在那个从旧石器时代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进程中,人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正经历着艰难的蜕变,总有一个人要率先为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物去定义、推演、预知,时代呼唤的伟大战士伏羲出现了,他仅用两条短线“—”和“--”的组合,就定义出“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八种自然现象,这样的认知方法具备了穿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当阴阳鱼如同渭河奔涌的样子出现在太极图上,华夏民族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实现了跨越式突破。而当地老百姓称呼伏羲为人祖爷,便是对他亲切的尊称和功绩的敬仰。 伏羲一画开天,华夏民族的文化出现了分水岭,一面是蒙昧,一面是文明。我想,这是伏羲在卦台山上俯瞰三阳川的灵感乍现,也是人们对新石器时代心智觉醒的崇敬之情。事实上,在卦台山出土的文物和与它直线距离相距七十公里的大地湾出土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佐证了在五千年前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的事实。在随后的岁月里,伏羲的部落沿着渭河,走向黄河,从黄土高原走向华夏大地,伏羲的足迹落在文明的史册上。而它的源头之光,就产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卦台山上。 奶奶去世后的那一年,我再一次登上卦台山。当我极目远眺我的村庄,那里,奶奶长眠于地下,她的身躯成了三阳川大地的一部分,而她心中的圣山——卦台山,始终屹立在三阳川西侧,这座曾经陪伴过我奶奶近百年的山,见证过伏羲一画开天的山,是我心灵的高山。